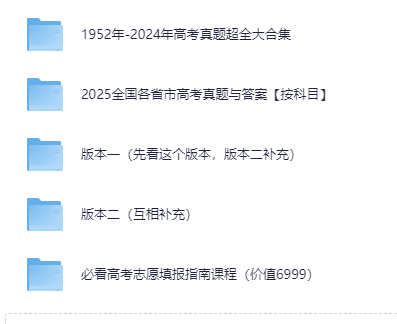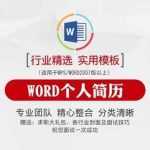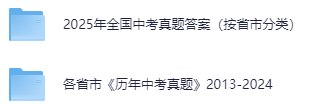刘浚的母亲,是宋文帝最宠爱的潘淑妃的。
潘淑妃有多受宠?我们知道一件事就可以了。袁皇后就与潘淑妃争宠失败而死的。
太子刘邵是袁皇后的儿子,所以太子刘劭对刘浚母子,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恨。在这种背景下,刘浚有两种选择。
第一种选择,就是历史上最常见的选择,依靠自己母亲得宠,与太子争夺皇位继承权。
因为,太子的母亲与刘浚的母亲争宠而死,太子上位后,难免会翻出历史旧账打击他们母子的。
第二种选择,就是主动与太子示好,尽力化解从前的恩怨;并且积极维护太子的地位。
我们必须得知道,太子的母亲(袁皇后)虽然是因为与刘浚母亲(潘淑妃)争宠而死,但潘淑妃并没有主动打击过袁皇后,一切仅仅是袁皇后争宠失败后,想不开气死罢了。所以,刘浚母子与太子的矛盾,并非不可化解的。
刘浚母子显然做了第二种选择,换而言之,主动与太子示好,尽力化解从前的恩怨;并且积极维护太子的地位。
史书是这样记载的:元皇后性妒,以淑妃有宠于上,恚恨而殂,淑妃专总内政。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。浚惧为将来之祸,乃曲意事劭,劭更与之善。
从历史去看,刘浚的这种选择,是非常值得圈点的。因为处于类似的地位,刘浚选择夺储的可能性实在太大了;关键是,夺储成功的可能性也太大了。
刘浚母子能拒绝夺储的选择,本身就证明他们并不是利令智晕的人,因为这种夺储行动一旦开始,就是一条不归路;成功了,自然什么也不用说;如果失败了,他们母子肯定会死得很难看。
我们有理由相信,宋文帝刘义隆最初看到刘浚母子能这样明事理,顾大局,肯定会感到很欣慰的。因为这是他家教有方啊!因为历史上了为皇位,而兄弟相残的人多的是,刘浚母子不恃宠而骄窥视皇位继承权,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。
如果故事只到此为止,相信刘浚母子写在历史书上,就可以成为宠妃或皇子的楷模。问题是,故事到此只是刚刚开始罢了。
这个故事后来的发展,显然超出了刘义隆的想象。因为刘浚没有因为自己母亲受宠,而心生夺储的念头,反而与太子走得越来越近。最后近得都有些让文帝刘义隆感到害怕了。
刘义隆对潘淑妃说:太子这样作,我可以理解,因为他是着急接班。虎头(刘浚的小名)这样做,又是图什么呢?
史书是这样记载的:上惋叹弥日,谓潘淑妃曰:“太子图富贵,更是一理,虎头复如此,非复思虑所及。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邪!”遣中使切责劭、浚,劭、浚惶惧无辞,惟陈谢而已。
的确,虎头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
恃宠而骄,是人的本能;换而言之,处于刘浚母子的位置,他们不去夺储,只有两种可能。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智慧低于常人,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的智慧超于常人。
潘淑妃能长年独霸后宫,本身就证明她的智力不会低于常人。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,刘浚的智力低于常人。从这层意义上,刘浚母子能拒绝夺储的诱惑,本身就证明他们都有着过人的智慧。
但处于那种年代,又深陷入权力漩涡之中,他们的智慧似乎没有让他们躲过悲剧的命运。
我们知道,刘义隆的身体并不好。有好几次都已做好了安排后事的准备。
有一次刘义隆感觉自己快死呀,所以害怕太子驾驭不了檀道济,于是就把檀道济杀掉了。
还有一次,人们都感觉刘义隆快死呀,所以刘义康一系(刘义隆的弟弟)竟然要忙着要抢班夺权了。
我们处于刘浚的角度去看一下,就可以发现。一边是动不动就病得快死的父皇,一边是野心勃勃的太子。刘浚选择站队时,自然会站在太子一边了。
刘浚与太子最初也并没有谋杀宋文帝的意思,因为宋文帝本身就动不动病得要死,他们实在犯不着对这样一个宋文帝动杀机。
在这种背景下,刘劭、刘浚最初的所作所为,并不是针对宋文帝的,而是针对皇叔和其它皇弟罢了。换而言之,他们积极发展势力,只是想保证在宋文帝去世后,能牢牢控制帝国罢了。
只是一直病得要死的宋文帝,却是活得越来越精神了。如果事情只是发展到这一步,事情还好说。问题是宋文帝看到太子势力如此不可抑制的发展着,心里自然会非常害怕,因为这样发展下去,太子随时可能会提前接班的。
我们知道,太子本身的势力与某个皇族亲王相比,就有着足够的优势;太子与另一个强势亲王(宠妃的儿子)穿着一条腿的裤子,那所代表的势力就更是惊人的了。
面对此情此景,宋文帝对太子的猜忌之心自然会越来越严重,但此时想通过温和的手段限制太子,似乎已不是可能了。于是皇帝与太子的矛盾开始越来越严重。
其实至此为止,太子与宋文帝的矛盾;与萧道成、萧赜、拓跋焘与太子的矛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。只是从前动不动就要死的刘义隆,现在身体却是越来越硬实;而太子虽然受到皇帝猜忌、打击,却也没有又怕、又气病死,在这种背景下,他们父子的矛盾终于愈演愈烈无可调和了。
事情发展到最后。潘淑妃(刘浚的母亲),似乎已意识到局势的危急,所以劝自己儿子赶快站在皇帝的一边。
但是刘潘淑妃万万没有想到,她这样作的结果,等于把一项最绝密情报透露了出去。因为她等于变相的告诉刘浚,皇帝已决定清洗太子一系了。
听到这个消息,刘浚自然是大吃一惊。但刘浚应该如何去做呢?继续站在太子一边,还是赶快站在皇帝一边。这种两选择对刘浚而言都是痛苦的。
选择及时站到皇帝那一边,显然意味着太子刘劭死路一条。因为废太子是没有活命希望的。而对刘浚,似乎也是看不到什么希望的,因为他从前的行为,从情理也许可以原谅,但从法理上,恐怕随便抽出哪一条也是死罪;即使因为自己母亲的原因,他可以逃过死罪,恐怕也不会有什么政治前途了。从这层意义上,刘浚在这个关键时候选择出卖太子,意味着变相杀死自己的大哥,更意味着主动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。
于是刘浚变把自己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情报,告诉了太子刘劭。于是太子刘劭终于决定先下手为强了。
处于太子刘劭的角度去看,他的选择虽然大逆不道,但是他不杀文帝,自己就是死路一条。因为废太子,好像是没有活路的。
处于刘浚的角度去看,他的选择虽然不可理喻,但一步步走到此时,他好像也真没有太多的选择,因为他在太子的贼船上走得实在太远了。
我无意说,刘劭、刘浚杀父的行为有理。我只是想说,他们的这种行为,是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里。而在那个年代里,兄弟、父子相争、相残似乎不是什么新鲜事。
我们常常把这一切,归于了那个时代的道德沦丧,却忘了那个时代的利害关系,常常会让父子、兄弟陷入囚徒困境中。换而言之,他们谁也不能真正信任谁,谁也可能被对方先下手为强了。

 司马迁错了?还原真实的秦始皇陵:被误解千年的历史真相
司马迁错了?还原真实的秦始皇陵:被误解千年的历史真相 东昏侯萧宝卷 真有史书上说的那样昏吗
东昏侯萧宝卷 真有史书上说的那样昏吗 石敬瑭上位 军方大佬一个比一个狂
石敬瑭上位 军方大佬一个比一个狂 李嗣源借力王淑妃 后宫干政为哪般
李嗣源借力王淑妃 后宫干政为哪般
pdf-150x150.jpg)